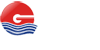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卓韦 于 2010-1-20 13:53 编辑
网上诗话(68)刘章的“白话律诗”
[关键词] 现状 果色初露 曙光在前
◆ 程文
刘章也是位“白话律诗”的尝试者和实践者。1997年12月,他在《刘章自选诗·白话律诗尝试集》(18首)序中说:
“我在1987年曾写过一阵子八行诗,前后各两行,独立,中间四行连排,试图写白话律,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中间四行不对仗。近日,正欲重新实验时,刘征兄寄来了《八行体诗一束》,借鉴旧体诗七律,提出了自己的规定性。”“我便积极配合尝试,我只讲对仗、排比,讲押韵,不讲节拍限制,只是在一首诗有规矩可循(如首两行与尾两行一致)。只为尝试,不计成败。”
这段文字,我们既可以看到刘章继承唐代律诗传统创建新体格律诗的曲折经历,又可以看到他理论认识上的提高和不断进步。的确,包括对仗、排比、复唱以及重章叠句之类具有格律属性的修辞方式,在我国诗经、律诗乃至词曲里,都是被历代诗人极为重视的,到律诗时代已经与字数、平仄等一起规定在格律内容之中了。当然,对新诗来说,已经是久违的很少谈起的事情了。然而,刘章的这些引进与尝试,重新使新诗与古典诗歌接通了血脉,所写新诗的面貌焕然一新了。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感到久违了的民族诗歌又出现了曙光。
㈠ 先看成熟的整齐体“白话律诗”:
少年|扮老头‖往往|很像,
老人|扮少年‖绝难|传神。
容易|学得的‖老成|持重,
不可|模仿的‖儿童|纯真;
爱护|少年的‖无价|天性,
珍惜|自己的‖半点|童心……
流水|送落花‖一去|不返,
太阳|落山后‖再恋|星辰。
——《观孙学老头有感》是首上“五”下“四”的“五四体”四步九言诗,而且全诗各行里的两音音步与三音音步的排列顺序统一为:2|3‖2|2。——这岂不是格律十分饱满的新型格律诗吗?
草草|写出‖人生|悲剧,
精心|构思‖命运|儿戏;
二十|元钱‖离的|价值,
半块|小镜‖聚的|希冀;
痛苦|之果,‖谁种?|谁收?
人生|之路,‖何来?|何去?
山高|路窄,‖长风|浩浩,
林密|云深,‖哭声|细细……
——《弃婴》则是首上“四”下“四”的“四四体”四步八言诗,全诗只用一种音步,各行音步排列自然一律是:2|2‖2|2。
树叶|落地的|时候,
很像|一只只|小鸟。
叶面|紧贴着|地面
叶柄|翘望着|天空,
好像|扑向了|大地,
又像|等待着|乘风。
树叶|落地的|时候,
不尽|缠绵的|诗情。
——《树叶落地的时候》则是首三步七言诗,而且全诗各行里的两音音步与三音音步的排列顺序统一为:2|3|2。
——上面这三首整齐体的“白话律诗”,无论诗行的构成、诗节的安排,还是对仗与韵律等的运用,都明显地看出是属于现代语言条件下的新格律诗,明显地看出其与古汉语条件下的五七律之间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渊源关系,看到了“白话律诗”对“文言律诗”传统的充分继承以及创造性的发挥,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㈡ 再看属于由整齐体变为参差体的“白话律诗”:
所以由整齐体的五七律变型为参差体“白话律诗”,原因就在于作者“只讲对仗、排比,讲押韵,不讲节拍限制”。请看诗例:
归乡|依旧是|思乡梦,
醒后|倍觉得|乡思重!
醒时|思乡‖恨见|云影,
梦里|归乡‖愁无|脚踪;
出山|泉水‖分秒|不停,
归林|宿鸟‖夕晖|消融……
明日|又将是|离乡行,
云山|几回做|送还迎。
——《归乡》首尾4行是三步八言诗行(2|3|3),而中间对仗或排比的4行,却是四步八言(2|2‖2|2)诗行。诗行字数虽然相同,但是音步的数量却不相同了,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因为古今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穿过|一村村‖美丽的|梦境,
踏碎|一程程‖晶莹的|雪花。
急急|切切,‖回去|看望|妈妈,
仿仿|佛佛,‖至今|还未|到家;
又饥|又困,‖当时|情景|狼狈,
难追|难返,‖今日|回忆|潇洒……
走过|四十年‖人生的|道路,
留恋|十七岁‖苦乐的|年华。
——《夜归》首尾4行是四步十言诗行(2|3‖3|2),而中间4行却是五步十言诗行(2|2,‖2|2|2)。与前例道理相同。
这种情况更有甚者,下面的例子则走得更远,差异更大:
方言|很美,‖有滋|有味,
如四川|辣椒,‖如山西|陈醋。
讲述了|许多‖古老|故事,
走出了|许多‖风流|人物;
一面|集结‖向心力|旗帜,
一面|通向‖凝聚力|大路……
方言|很美,‖有形|有状,
在吴越|秦晋,‖在三江|五湖。
——《方言》首尾4行是分别用四步八言(2|2‖2|2)和四步十言(3|2‖3|2)两种长短诗行构成的反复;而中间对仗的4行却是用第三种诗行:四步九言(3|2‖2|2或2|2‖3|2)。
这样看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律诗”与“白话律诗”的诗体“变型”或“变体”问题。
如众周知,律诗里无论五言律诗还是七言律诗,都讲究限字,五律一律五言,七律一律七言,都属于整齐体诗歌,没有字数多少不一的参差体。而“白话律诗”里却出现了各样的参差体,这样再名之曰“白话律诗”,显然不甚理顺。于是乎有人称之为“变型”或“变体”。
对此,如何处之?想来作者一定会有通盘打算,或者不改变现状,保持这种正体与“变体”共存的现状;或者从根本上解决,运用现代的完全限步说来处理,即对诗行实行全面的限步,即不仅统一诗行的字数,而且还要同时同步地统一诗行的步数。比如,就像开头列举的《观孙学老头有感》那样,每行都统一为四步九言诗行,或者像《树叶落地的时候》那样,每行都统一为三步七言诗行……这样依然属于整齐体的格律诗。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方式。
这还需要通过长期而广泛的创作实践来琢磨、验证和探寻。
由此可见,刘章在长期的新格律体试验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首先,刘章不畏艰险,敢于带头进行新诗的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探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且我们值得虚心学习。在长期的新格律体试验过程中,他已经熟练了驾御新格律诗语言以及各种基本格律因素的能力,能够熟练地表现和抒发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内容以及特定的诗情。至于“白话律诗”的格局与定式将来如何,我想先生胸中自有成竹,一定会通盘地长远考虑,统筹处理的。拙文这里只是现状的具体分析而已。
2008·9·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