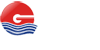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卓韦 于 2010-1-4 07:09 编辑
网上诗话(33)音步、顿与大顿律
◆ 程文
[关键词]
音步与顿的区别 大顿律作用
一 · 音步与顿不容混淆
音步与顿的概念,直到今天,人们的认识还往往混淆不清,叫法多多,尚未统一,最糟的是常有人把音步和顿两个角度不同、内涵与外延都有差异的概念混为一谈。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理论研究的不必要纠缠,也不利于新格律诗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格律诗与自由诗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讲究节奏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节奏的形成,涉及音节、音步与顿、音律与韵律、诗行与诗节以及格律修辞等各种基本格律因素,其中音步作为组织、量度诗行并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其基础性作用于方方面面、不可或缺。因此,同时也是吟诵的节拍或尺子,也是伴舞的步谱。故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称之为音步、音尺、音组或者拍。 “饶孟侃和闻一多称之为音尺,孙大雨和卞之琳称之为音组,陆志韦和胡乔木称之为拍,都是一回事。”(邹绛《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序》)
所谓“节奏”本义是指声音响停、长短和轻重周期性连续所形成的规律。所谓“节”,是指节奏中声音的停歇;所谓“奏”,是指节奏中声音的发声。音步和顿的关系,某种意义说,就是节奏中“响”与“哑”、“长”与“短”、 “轻”与“重”或“形”与“影”的关系。音步与顿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响哑、实虚、阳阴之分,不可替代,又有相反相成、缺一不可、对立统一的一面,可以说两者是一对孪生的兄妹。正所谓有“奏”(响)有节(哑)才有“节奏”。
以白话文为语言基础的新格律诗,在抒情表意的过程中因意念关系与语法条件而形成了自己的音步体系:常用的基本音步是以两音音步为主,三音音步为辅;不常用的特殊辅助音步有单音音步和新生的四音音步。何其芳、邹绛等也都看到了这个现实。何其芳《再谈诗歌形式问题》说:
“每顿字数不定,从一字到四个字都可以”。邹绛在上文中说:“以两个字、三个字组成一顿的最多,也有一字一顿,或四个字组成一顿的。”
两位话里的“顿”是指音步,因为用几个字组成的只能是音步,而“顿”是表示音步之间停顿和间歇的时间概念,只有时间长短的不同。周煦良说得好:“音组(音步)是指几个字作为一组时发出的声音,‘顿’是指‘音组’后面的停顿,或者间歇;换句话说,‘顿’是指一种不发声的状态。这种区别当然是相对的,因为没有顿就辨别不出音组,没有音组也就显不出顿……”(《文学评论》1959年第三期第29的注①)
有人总觉得叫音步“容易和轻重格或抑扬格的英诗中的音步相混”。其实“音步”最早源于以长短音为特色的古希腊诗歌,英诗借鉴和效法古希腊诗的先例,以其轻重音与音步融合亦称之为音步,可见不必强求各民族语音特点完全一致。我国的律诗从平仄律角度,也将五律的三个音步(2|2|1)分别称为“首节|腰节|尾节”,将七律的四个音步(2|2‖2|1)分别称为“顶节|首节‖腰节|尾节”(尾节都是单音音步)。我国汉语轻重音与长短音不突出,而平仄音却是可以开发的,特别是新诗的长短音步多达四种,充分规范发挥长短音步的功能,就可以强化诗的节奏,弥补轻重音、长短音的不足。
命名还要兼顾其在本系统内的适用范围及其可能性。比如“四步九言诗”、“四步十言诗”之类概念里的“步”就不宜用“组”、“尺”来替代,也不便于与外国格律诗接轨。
顿是紧随音步之后产生的表示停顿和间歇的时间概念,而且因为位置和停歇的时间不同而分成四种:诗行之尾的顿,除了句顿(句行之末,即一句完了之处)就是逗顿(因为多数诗是有标点的,故不必另设符号);诗行之中除了有普通的极短暂的小顿(用“|”表示)之外,在四步以上的诗行之腰一般还有个停顿时间大约半个逗号多一点儿的大顿(或叫半逗顿,用“‖”表示)。大顿的作用,除了有力地强化诗的节奏之外,还有促进“子诗体”成熟的特殊作用。比如四步九言诗的“五四体”和“四五体”,四步十言诗的“五五体”、“四六体”和“六四体”……
二 ·大顿律与半逗律
在顿世界里,无论行尾的逗顿、句顿,还是行里的小顿、大顿,都涉及其他基本格律因素,关系到诗歌节奏的和谐与鲜明。就停顿时间以及所处位置而言,大顿尤其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法国格律诗不讲究音步,但却十分讲究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从二音诗到十三音诗都有,使用最多的诗体当然是十二音诗。为了促进和强化诗歌节奏的和谐与鲜明,法诗严格规定了“半逗律”,即在所有诗行的中腰用相当半个逗号的停顿将其分成前后两半,形成个特殊的音的规律。对于十二音诗来说,即在前后两个六个音节之间使用,行行如此便形成了“半逗律”。在法国古典主义的诗歌中,半逗律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破坏的。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诗论奠基人波瓦洛,在他的那部以诗体写成的被推崇为古典主义诗歌法典的《诗的艺术》中,特意提醒诗人必须遵守半逗律:
你只能贡献读者使他喜悦的东西。
对于诗的音律要求应该十分严厉:
经常把你的诗句按意思分成两截,
在每个半句后面要有适当的停歇。
事实上,我国七言律诗也有个“上四下三”之说(“诗经体”与五律应该说并不明显),这便是汉语旧诗的“半逗律”(“2|2‖2|1”),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大顿律”。如:
昔人|已乘‖黄鹤|去, (逗顿)
此地|空余‖黄鹤|楼。 (句顿)
黄鹤|一去‖不复|返, (逗顿)
白云|千载‖空悠|悠。 (句顿)
顶节 首节 腰节 尾节
——崔颢《黄鹤楼》
我所以主张叫做“大顿律”,是因为这是在诗行大顿处统一形成的音的规律;停顿时间虽然都是相当于半个逗号,但是所在位置不一定都绝对是诗行的正中间。请看流沙河《重访杜甫草堂》:
八九树|梅花,‖陪伴着|你那|小堂|低舍,
两三声|啼鸟,‖问候着|我这|锦城|归客。
二十年|远别,‖你依然|炯炯|目光|直射,
恨透了|奸贼,‖销磨掉|铮铮|英雄|豪杰。
另外,个别诗篇,如公刘《铁的独白》每行都用了两个大顿:
领我|去吧,‖领我|去吧,‖领我|去到|车间
——可见沿用“半逗律”,一是概括不了我国新诗“大顿律”的全部内容,二是不如“大顿律”更符合由大顿而来的实际。
诚然,不是所有的诗都存在使用大顿律的条件,一般三步两步诗就没有;就是有条件的四步以上的诗,还需要作者具有驾御大顿的能力。林庚强调半逗律的作用,是个贡献,并没有质的错误。应当承认“大顿律”不仅是一种强化、活跃和丰富新诗节奏感与音乐美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能够促进“子诗体”成熟的特殊的基本格律因素。林庚先后提出的“九言诗的‘五四体’”和“四五体”,就有力地促进了“‘五四体’四步九言诗”和“‘四五体’四步九言诗”两种“子诗体”的孪生。对新诗的发展和繁荣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戴望舒《烦忧》
案上│几拳‖不变的│奇石,
何如│天空‖善变的│浮云?
囊中│几粒‖有限的│红豆,
何如│天空‖无数的│繁星?
——刘大白《旧梦之群·六十五》
同样,有了大顿的规律安排,四步十言诗才孪生了“五五体”、“四六体”和“六四体”三种“子诗体”。林庚《北平情歌》就是首上“五”下“五”的“‘五五体’四步十言诗”:
冰凝在|朝阳‖玻璃|窗子前,
冻红的|柿子‖像蜜|一样甜。
街上有|疏林‖和冻红的|脸,
冬天的|柿子‖卖最贱的|钱。
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里说:“所以,音步和顿的适当运用,而不是押韵,在建立新格律体上占关键性的位置,因为有如韵式一样,音组也可以容许各式各样的组合和变化。”
200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