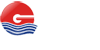|
网上诗话(1)写诗与人格
◆ 程 文
[关键词] 写诗和人格 格律和人格
有诗友在中华诗词网上跟帖说:
“诗从现实来,格律从诗‘种’来。现在的问题是:先写诗,后精格律?还是(把)先精格律诗降到次要地位?格律是把双刃剑,既是美女也是毒蛇。她起规范作用也扭曲作者的思想和灵魂。她能将伟人捆成肉棕。我们千万不能拜倒在格律的石榴裙下,但我们能够和她一起翩翩起舞。要写诗就要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要抱牢格律弃了人格。”
“诗从现实来,格律从诗‘种’来。”诗歌的内容,的确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再现;而诗的格律形式则是各国人们根据本民族语言语音体系的特点,在长期诗歌实践中逐步总结与规范出来的写诗规则。各国的语言不同,格律规则自然也不尽相同。但是作为自由诗与格律诗这样两种形式对的诗体,形式主张却是相对的,所以逆向地说“格律从诗‘种’来”也有些道理。自由诗是自由的,而格律诗则必须遵守格律规则,在规则中谋得驾御自由。然而两者既然都是诗歌,自然就有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都要讲究意境、意象和比喻以及修辞,也必然都要讲究诗的节奏与旋律。自由诗也不例外,也不能任其节奏凌乱无章,不堪卒读。所以,讲究节奏美是一切诗体的共同追求。有人说自由诗的节奏具有天生的自然美,然而“野马撒踢”的凌乱不堪者也并不少见。所以从古到今诗人们不断地总结和发展格律规则,形成了我们民族格律诗歌的光辉历史。应当看到,经过恰当的格律规范而形成的节奏总是以具有自然美者为多。这就是前人所说的经过“点化”后的自然,由“不隔”(平易)——“隔”(加工)——“不隔”(平易)。格律诗讲究格律规范化,就是这种“点化”过程。可见,自由诗与格律诗实现节奏与旋律自然美的途径和手段是不同的,然而目标是一致的。
某种意义上说,自由诗与格律诗既是相反相成的,又是相互促进的。两者的相互制约,也没有什么不好。诗歌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由诗与格律诗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又相互补充的发展与繁荣史。关键是不要把格律与节奏的自然化绝对地对立起来,要一分为二。试想:如果没有唐代的律诗,怎么会有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诗经体、唐诗、宋词和元曲,怎么会有我国辉煌的民族格律诗歌的悠久历史?怎么会出现诸多杰出的人民诗人?
“现在的问题是:先写诗,后精格律?还是(把)先精格律诗降到次要地位?”这个问题,不应该把诗歌创作与格律研究对立起来,应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切实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必硬性规定什么先后,这不是计划生育。从总的看,还是共同发展并肩前进为好。
另外,我国“五四”时代的新格律诗人,如闻一多、刘大白、朱湘、戴望舒、许志摩等,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诗体的“大解放”,在创作自由诗的同时,也都感到了新诗体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他们首先大胆地进行了新诗体的探索。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便胡适和郭沫若的《尝试集》、《女神》里,不是也同时存在《蝴蝶》、《女神之再生》那样的格律体新诗吗?
值得注意的是,古诗词与新格律诗是有渊源关系的。新诗的格律是在即将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长期熟习和把握了古今语言及其格律条件的基础上,继承了古典诗歌格律中尚有生命力的精华,紧密地结合了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现代语言及其格律条件,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创作实践,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拙著《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一书就搜集了“五四”至今154位新诗人的357首成熟的格律体新诗(逐一进行了格律分析),提供了足够的诗证,我们已经不是从零开始了。由此可见,今天的诗人应当多学多写点诗词,对自由诗的规范化,对格律体新诗的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建设,都是大有益处的。且不说幼年读过旧体诗词的那些老一辈诗人,而像梁上泉、琼瑶、刘章、万龙生、王端诚等这些诗人,其新格律诗所以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兼通古今格律诗歌,这才有能力创作出新体诗歌来。
至于认为“格律是把双刃剑,既是美女也是毒蛇.她起规范作用也扭曲作者的思想和灵魂”的说法,此话不无道理。其实,关键就在于树立一种怎样的格律观。格律唯一论格律至上论者,搞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当然是行不通的,那将导致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一并毁灭,即所谓“她能将伟人捆成肉棕”。但是,格律并不是冰毒,不能认为一沾上就会变成大烟鬼。不能搞形而上学,要严格地进行具体分析。要知道,无论哪种文学形式,都讲究进步的内容与完美形式的高度统一,弱化内容或形式都一样是没有道理的。当今的某些诗歌,所以分不清是散文还是诗歌,关键就在于漠视了诗歌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反对形式主义是对的,正视形式的作用也并不是错误的。要知道,只有用优美的外衣装饰了你的思想,人们才会倾听你的诗。特别是新体诗歌尚未成熟的今天,吕进先生曾这样强调过,“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无体则无诗”。写诗的人,如果对诗的形式认为是可有可无的,那是无知和悲哀的。诗人不要怕戴形式主义的帽子,特别是在现在所处的诗体建设时期。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不是多次被打成“唯美主义诗人”吗?历史是客观和公正的,多次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今不是都成了极左的笑料了吗?不仅丝毫也没有掩盖他的声誉,反而使他人格的光辉更加灿烂辉煌。随着新格律诗的发展与成熟,闻一多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反而成了公认的新格律诗之父!
可见格律不是洪水猛兽,不必谈虎变色,只是诗歌的形式问题而已;即便是形式主义也只是属于文艺思想或学术思想问题,谈不到“人格”问题,讲究和主张格律不等于就“弃了人格”。可要知道:“老去渐于诗律细”的杜甫,一直都是讲究格律的,能说他这是人格问题吗?今天我们讲究和主张格律,是以更好表现和讴歌现实生活以及繁荣新诗为前提的。因此,一定要解放思想,坚决贯彻和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大胆发展繁荣我们的当代诗歌。只要“石榴裙”是纯洁美丽的,何妨“和她一起翩翩起舞”,哪会因此就一定玷污了我们的人格呢?
倒是“写诗”与“人格”息息相关,正所谓“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写诗”和“格律”的内涵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写诗”是诗人通过创作诗歌来抒发自己对生活或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过程;“格律”充其量是在创作格律诗过程中所应用的格律规则。至于运用得好坏,那要归结到作者的创作思想,怪不得格律本身。律诗就那些规则,为什么有用得好坏之分,创作思想不同罢了。
其实,上面讨论的实际上是“格律”与“人格”,两者风马牛,是属于两个问题,其实质是联系不起来的,没必要硬扯在一起。比如说,由古体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发展到近体诗(五言律诗、七言古律诗),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绝不能因为是格律问题就认为是一种后退。
新诗要摆脱现在的边缘化状态,必须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只有百花齐放了,当代诗歌才能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2007·5·8 |